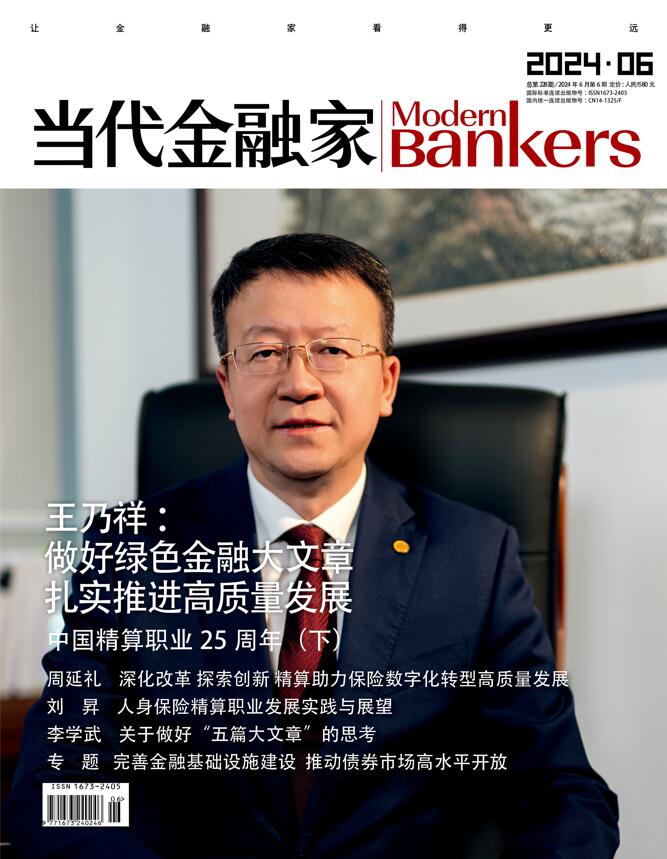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下,无论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还是国际金融,均不同程度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和问题。但也恰恰是在同一背景下,人民币的国际化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既是中国经济应有国际地位的内在反映,也是中国政府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的积极效果。未来十年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十年,“一带一路”的提出和积极推进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战略支撑。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低到高,必须相应经过支付货币也就是贸易货币、投资货币或者说完全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这样三个最基本的阶段。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都可以实现前两个阶段,从而成为具有支付手段与投资工具这两大基本功能的国际货币。但能否成为储备货币才是衡量一国货币是不是成为真正国际化货币的最关键因素。而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最基本的条件不是能不能用来支付,也不是是否完全可兑换,能够用来进行跨国自由投资。毫无疑问,这两点只是基础条件,因而只是前提条件。此外必须还要具备必备条件,而这个必备条件只能是主权货币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特定地位,换言之,也就是一国货币作为主权信用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程度。 截至目前,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只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瑞郎。其中除瑞郎的情况特殊以外,其他几种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最关键的就在于各主权国家和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国(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具备了相应的地位。相反,新加坡元、新西兰元、港币等,虽然也都具有较高的国际信用评级,但局限于其经济规模,都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而也就都不能成为真正国际化的货币。经过三十几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正是这种特定的国际经济地位,为中国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实现人民币的真正国际化,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争取目标。 未来十年,从国内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社会条件的全方位综合考量,我们看到,至少存在三个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提升,作为内在基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未来几年,随着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推进,在渡过目前的难关后,中国经济实现结构升级,中国经济不但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可以在新的增长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长波周期。 一般分析,在既定的现有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中国本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底部会在明年,也就是2017年的第一或第二季度出现。而中国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大概要到2018年下半年。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最早在2017年下半年,最迟在2018年年底前,就将重新迈向新的增长阶段。而在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至少包括四大基本要素,一是城镇化,二是消费升级,三是全方位结构调整所推动的产业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形成的全面创新能力,四是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这样,最迟到2025年也就是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就可能达到或接近美国的规模,世界经济就有可能真正进入“G2”时代。显然,正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这种强劲增长势头,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人民币最终成为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在未来5~10年总体上仍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已经萧条了接近十年,目前仍看不到最终摆脱萧条的明显迹象。从更深层视角来审视全球经济,不难发现,全球经济实质上也与中国一样,处于特定的“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振荡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样一个特定状态之下。这种“三期叠加”反映出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要求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必须具备多重视角才能够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面对的“三期叠加”问题,要求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要求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必须积极推进类似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还没有进入积极推进改革的阶段。虽然美国在去年已开始加息,国际经济学界也一度认为美国进入了加息周期。但进入2016年,一直到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连续三个季度陷入1%左右的低速增长,完全没有了2014年后西方世界所吹嘘的“一枝独秀”。当然,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也就不能不表现得极度谨慎,从而使得美国的总体利率水平仍然徘徊在极低水平。至于再平衡,在美国国内更是逆势前行。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国的优势明明是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但奥巴马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重新振兴制造业,这就在虽然能够确保美国的非农数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设置了障碍。至于欧洲和日本,情况就更糟糕了。不但谈不到加息也就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而且还得纠结如何继续推进量化宽松的问题。而继续沉迷于宽松货币的刺激,当然也就谈不到再平衡了。 毫无疑问,在此情形下,一旦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中国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再平衡阶段,西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再一次被拉大。就目前而言,美国不到3%,欧洲与日本0到1%的增长率,与中国的6.5%就已经差距很大了。一旦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长波周期,两者的差距还会进一步加大,为中国较为顺利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技术上看,美欧日继续沉湎于宽松货币政策,继续奉行目前的超低利率,还会与中国人民币的利率形成一个较大的息差,这也成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进程,以及国际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全球经济衰退要求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同时,全球贸易的萎缩和金融业全球化进程的倒退要求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业也要再平衡。从更深层次看,美国退市所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混乱反映出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混乱与失衡。显然,在这方面,更需要再平衡。 全球治理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重视。2000~2015年,以现价计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的占比从20.3%上升至39.3%。同一时期,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由32.3%上升至46.1%。但是,新兴经济体货币地位并未同等幅度提高,2013年新兴经济体货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占比不超过10%。这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衡。 至于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看,情况就更为明显。2008年至2012年,在美欧日全面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超过50%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其中仅中国自己就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增量。近几年来,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超过25%,连续几年都高于 “一枝独秀”的美国。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对比如此清晰、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远远低于美国,甚至还远低于英法德日等国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治理体系的不合理与失衡。 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国际化,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必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推进,才能达到预期的积极效果。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或者作用力和作用方向相反,其结果就只能是日本的例子。当年美国在经济实力远超英国的时候,也还是要依赖马歇尔计划的推进,凭借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两大支柱,才能最终取代英镑,实现美元的国际化并成为全球的霸主,就是一个明显的成功例证。 近年来,中国政府强力推进的各种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其实质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再平衡与合理化,从而在更高层面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竞争力。当然,这些举措真正发挥实际效果,需要5~10年的时间。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局、从区域到洲际的由低到高、由浅层次到较深层次的有序演进进程。 在目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和整个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体系中全面崛起的内在要求,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会在新兴市场和整个发展中经济体中首先得到确认。而“一带一路”建设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和愿景。商务部2015年3月发布的 “一带一路”路线图明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路线图要求,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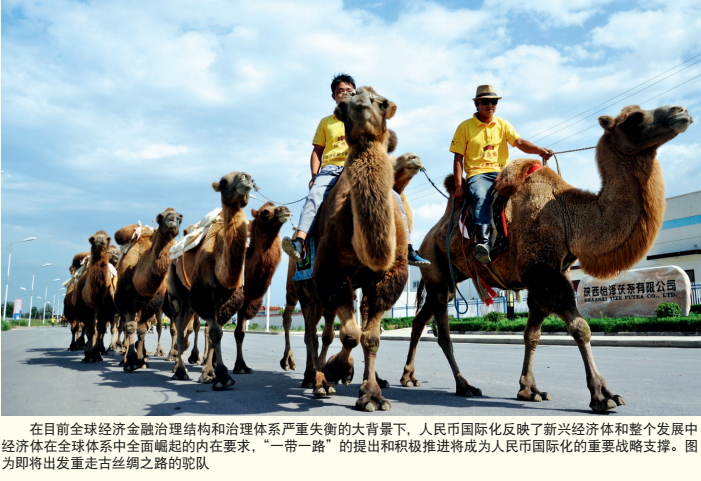
上一篇:求木之长 必固其根 新常态下的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管理
下一篇:“过来人”说:信托型ABN的实践及启示